——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早期近代及近代的社会阶层,我们发现其间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质的相异。劳力者与劳心者的界线,儒家中国可能比西方来得清晰;但这样的界线,在所有的前近代与近代的文明社会差不多都存在。即使在现代的北美,虽然对劳力者的偏见已是最少的,但社会阶层体制的根本区别,仍在白领与蓝领职业之间。儒家传统与价值,可能会对富人在得以进入统治精英时造成较大的压力,但同样的驱策与社会弱势情结,也在大多数前近代与近代社会的新富(nouveaux riches)身上可以看到。教育,或更准确地说大学学位,在最「物质主义化」的北美社会阶层,越来越重要。
——何炳棣分析了进士及举贡共约四万个案例,发现这些人祖上三代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远远超过英国十八世纪的情形。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钱财本身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它必须转化成官员身分,才能让人充分感到钱财的力量。
——精彩片段
按:该书曾在硕士期间读过英文原版,并写过一篇读书笔记。读过此书方知什么叫做“大作”!作者功力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二十世纪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阶层间的上下流动,《明清社会史论》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巨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运用近百种明清两代的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进士同年齿录和晚清若干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这批量化的统计资料构成了《明清社会史论》的经线,有系统地呈现明清两代间,初阶、中阶和高阶举业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何炳棣分析了进士及举贡共约四万个案例,发现这些人祖上三代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远远超过英国十八世纪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一书里运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传记、家谱、社会小说和观察当代社会与家庭事务的著作等,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纬线。《明清社会史论》探讨了个人与家庭的地位转移、社会流动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会概念与迷思。除了从明清科举观察社会流动外,何炳棣也讨论了清代晚期所广泛施行的捐纳制度,如何使富与贵紧密结合,且影响力量趋强;造成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同时,何炳棣在书中不但处理向上流动,也讨论向下流动及其导因,《明清社会史论》亦有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
《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社会流动,根据的样本数量极多,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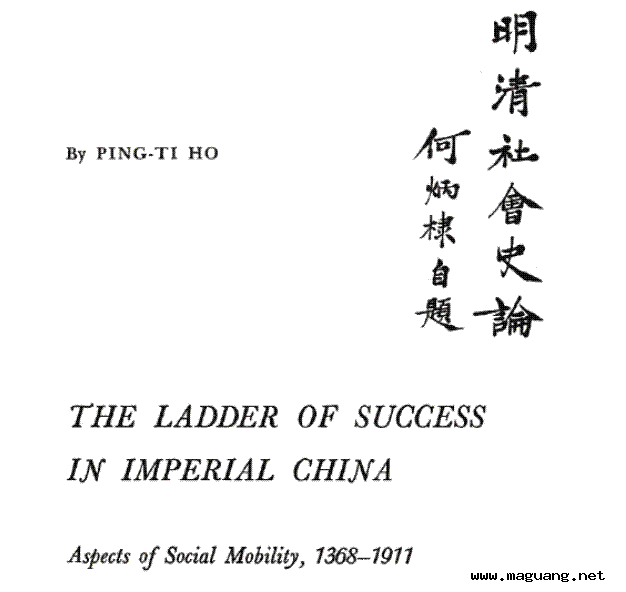
作者何炳棣(Ping-ti Ho)简介
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2012年卒于美国加州尔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34年入清华大学,1943年获清华庚款公费留美,师从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国农业经济史,1952年以〈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研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5年芝加哥大学聘为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
何炳棣治中国史,善用交叉学科知识与理论诠释关键史料。早年选择经济运作、社会结构,晚年钻研思想源头,皆为直指历史上影响时代脉动的核心问题。其名著《东方的摇篮》以充实的古代文献联系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知识,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皆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一源说的代言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亦为之折服。何炳棣之《明清社会史论》则运用社会分层化和社会流动理论,解释明清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身份意识的紧密联系,并将中国史从局限于区域研究的「汉学」,推到世界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西方学界主流殿堂,深受到西方学界肯定。

年轻时风华正茂的何炳棣教授

何炳棣教授晚年近照
译注者徐泓简介
1943年12月25日生于福建省建阳县,获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士、文学硕士及国家文学博士。现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及暨南国际大学退休荣誉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艺术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兼人文学部创设学部部长及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署理院长,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创所所长及系主任、教务长及代理校长。教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是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已发表明清盐政与盐业、明代社会风气、明代婚姻与家庭、明初国内大移民、明代城市及明清史学相关学术论著八十余种、学术评论三十余篇及历史普及读物三十余篇。

徐泓教授在书房
《明清社会史论》序
汪维真研究乡试解额,沈登苗研究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进士的地域流动,曹国庆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与夏维中研究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分析其数量众多的原因。其他地区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学者研究。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外,近年来有关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论著与论点,多与何教授相似,不过在资料的运用上有新进展,如对于现存登科录的调查整理及个别登科录的考证,近年来也颇有进展。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编印《明代登科录汇编》。2006年,宁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明代科举文献汇编,给学者们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与科举相关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对译注工作,大有助益。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此期间这个研究领域虽有上述的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教授的《明清社会史论》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韩文译本问世,但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实为一大憾事。泓最初读到何教授的巨著,是1965年的夏天,刚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班,所长刘寿民(崇鋐)教授将何教授送给他的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赐赠于泓。于是开始一页一页地读,初读英文写的中国史论著,最头痛的还不是英文,而是中国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与书名等专有名词,如何从英文还原为中文,尤其这些字词,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试着猜,猜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就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边看边试着翻译,居然译了四章半,后来因为忙着写论文而中断。泓之治明清盐业史,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与博士论文《明代的盐法》实受何先生大著〈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与《明清社会史论》启发,是从中得知什么是盐户、灶户,什么是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明清盐业与盐商在中国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生产与运销的研究。取得学位以后,有幸留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由于教学工作忙碌,也就搁下翻译《明清社会史论》的工作。
时值七十年代前期,正是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高潮,许多留美学人学生不满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软弱,而投身运动;遭国民政府或吊销护照,或视为拒绝往来户,何教授便是后者。当时国民政府对外虽软弱,但对内却很强硬,台湾在威权统治下,校园气氛甚为严峻,尤其身为学术教育界龙头的台湾大学,更是陷于「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学系事件,两次整肃之后,几乎完全改组;继而传说矛头指向历史系,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为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当然不宜再谈他的著作。直至八十年代后期,解除戒严,何教授也恢复每两年回来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权利,泓乃重拾旧译稿,以完成这一对泓学术生涯有重要关键作用的工作。无奈当时承担学术行政,正负责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与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担后,荣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钱致榕教授与校长吴家玮教授找了去创办人文学部;1993年底回台以后不久,又为袁颂西校长找了去创办暨南国际大学的历史学系与研究所,并担任教务长,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后,代理校长承担校园复建及延聘新校长等善后工作;沉重的学术行政工作,阻挡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转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的教职,教学工作单纯,遂能重拾研究写作工作。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是刘寿民老师创办的,泓拥有的何教授《明清社会史论》,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的业师和系主任刘寿民老师的,后来刘老师赐赠予泓,真是机缘凑巧。于是重拾旧译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业。不久,又蒙何教授约见,鼓励泓继续翻译,并惠允协助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随后又获国家科学委员会赞助此翻译计画,工作于是再度展开。
《明清社会史论》于1962年出版后,何教授又获得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与会试齿录、举人乡试录、贡生同年齿录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见到四种明代进士登科录等新资料,1967年第二版即据以修订,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数据,并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修订版与1962年原版中本章的内容有所不同。本译文即以1967年修订本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为底本。
这次翻译时,一一查对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献,还原于译文之中,若有出入则以「译者注」形式说明。由于这本书出版已五十年,此期间有不少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出版,与何教授对话,对于不同的意见及补强或修正的文献资料,也要以「译者注」形式说明。由于何教授征引之资料,有许多不见于台湾的图书馆,也一一向何教授请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协助,相信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不同于其他文字译本,而为较好的译本,也是较理想的中文版本。
《明清社会史论》目次
前言
第二版自序
第一版自序
译者序: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会史论》
目录
图表目录
第一章 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
第一节 基本反论
第二节 社会阶层
第三节 教育与财富同为决定社会地位之主要因素
第二章 社会身分制度的流动性
第一节 法理上缺乏对社会流动的有效阻碍
第二节 明代特殊身分进士的统计
第三节 社会文学所见身分制度的流动性
第四节 社会为儒家意识形态渗透
第三章 向上流动:进入仕途
第一节 史料的简要评述
第二节 统计分析
第四章 向下流动
第一节 抽样的家谱记录
第二节 人文环境
第三节 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
第四节 有限度的荫叙
第五节 财富的减少
第六节 家庭制度
第七节 小结
第五章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第一节 科举与官学
第二节 社学与私立书院
第三节 帮助应试举子的各种社区援助机制
第四节 宗族制度
第五节 刻书业
第六节 战争与社会动乱
第七节 人口与经济因素
第六章 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
第一节 各省的人口
第二节 以省分区分的科举成功者之地理分布
第三节 社会流动率的地域差异
第四节 科甲鼎盛的地区
第七章 概括与结论
附录 社会流动的案例选
引用书目
译者注与按语引用书目
《明清社会史论》书摘试读
第三节 教育与财富同为决定社会地位之主要因素
明清政府在法律上界定官僚体系各阶层的地位,明显地与其社会地位相符,但在我们研究平民阶层时,也发现各个主要平民群体间的法律与社会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传统中国政府既尊儒也「重农」;所以,在法律规定上有其强烈的偏见。不难理解,儒家政府把士民的地位置于其他庶民之上;因为士民是庶民中唯一劳心的群体。作为重农主义国家,农民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国家,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生存,就依存于农民的劳动之上。因此,农民虽然是劳力的,却比较能免受不平等的法律之害,常有权参加科举考试。《管子》这本书服膺的社会概念与孔子便相去不远,主张庶民应「世守其业」,严格地执行世袭的社会职业与社会地位,但也欢迎具「秀才之能」的农民子弟可上升为士,最终进入封建官僚之列。另一方面,工与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被视为财富的次要生产者与中间人;因此,在法律上给予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受到差别待遇及反奢靡法律的制约,禁止过于奢华的生活,其中较严重的是国家拒绝给予他们进入官僚阶级的权利;直到宋朝末年,法律还禁止工商之子弟参加科举。传统中国社会以工商为四民之末,轻视工商,歧视工商,这样的态度一直持续到近代。
但深入研究历史社会现象,却显示一个与法律文本不同的图象。西汉政府虽然采「重农抑末」的政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操兵器,又规定商人算赋加倍,子弟不得为官;但这些大资本商人、放高利贷者与工业家却「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教,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其社会地位等同王侯。其势力令人畏惧,对小民与平民是一大威胁,而被当代人称为「素封」,即「没有秩禄爵邑的贵族」。唐代的许多富商与大资本家成功地规避商人不得奢靡的禁令,过着只有上流社会才能过的生活方式。虽然宋代法律禁止工商子弟参加科举,可是有许多落第士子与官吏公开经商,而工商子弟设法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元代许多色目商人(来自中亚及中亚以外的非蒙古与非中国人)的势力更大,控制了国内外贸易,甚至政府的财政。明清时代,更取消最严重的歧视工商的禁令,这可以视为政府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工商迟来的认可。
接着讨论另一明清社会阶层的基本难题,那就是教育(或更具体的措辞:任官的机会)与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由于官方的法令与文书主要处理法律的社会阶层,因此微妙的社会现况,只能从社会小说与私人的文学作品中去找寻。以下所举几个事例也许过于极端,不能作为一般社会实情的反映,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还是可以帮我们强化理论的观察,认识到官职及可望得到的官职与财富,在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中相对的重要性。与反映社会类型的一些统计资料相对照后,我们就可以作出较平衡的估量。
我们很幸运地有《儒林外史》,这一部最能透露内情、最写实的小说,也是研究明清社会重要社会阶级不可少的著作。小说中许多令人大开眼界的片断之一,是关于一位贫苦的南方学者范进,这个穷童生,多年靠着他的岳父胡屠户为生,当他考上秀才,进了学之后,胡屠父对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这下子社会地位可算提高了一些,但家庭经济可以说毫无改善,连参加乡试的盘费都没有,等他出了考场,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一直要到中举人的消息传来,才大有改善,所以当他听说中了第七名「亚元」时,竟欢喜得疯了,报录的建议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就会好了,胡屠户却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女婿已是天上的文曲星了。这下全然改变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地方上一位也是举人出身和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马上亲自登门拜访,并送给他贺仪五十两与一所大房子;自此以后,地方上的小老百姓也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两三个月,家中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了。
在另一部社会小说《醒世姻缘》里也有一个细节不同的片段,这是个关于晁思孝突然改变命运的故事。他也当了多年的生员,是个财产有限的人,乡试屡考不中,后来因资历而成为贡生,使他能参加低级政府官员的特考,得了个知县。消息传来,地方上穷人也有愿为其仆人的,也有愿送土地给他,放债者愿无息贷款,晁家骤然间成为当地最富与最有权势的人家。上述一位南方、一位北方小说家分别独立地写出的两个故事片断,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通常更高的科名(举人)会导致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骤然提升。
明清社会中,财富本身并不是权力的根源,这一论点可在此进一步阐明。至少从明代中叶起,安徽南部山区的徽州府商人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商业集团之一,许多富商巨子以家财上百万两银子自豪。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谢肇浙,是一位广博的旅行家与不凡的观察家,他的那本包含天、地、人、物、事五类记载的著名笔记《五杂俎》,曾经是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晚明中国最受欢迎的指南。他在书中提到,徽州的一位百万富商汪宗姬的事例,因为他有钱,总是鲜车怒马,带了大批随从姬妾出游,有一次,路遇一地方官,未及时让道以致于长期诉讼导致破产。我们不能肯定汪氏是否曾捐过功名或官位,但显然财富的力量本身是敌不过官府权力的。
甚至有官衔的富商家庭,在特殊环境下,面对官府也是无能为力。徽州富商吴氏的事例更能令人大开眼界,这家人在十六世纪初正德年间,以盐商起家,一直很富有,到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初之际的万历后期,又常捐巨款从事地方慈善事业,包括建书院,刊刻十六部经书,免费提供给需要的学生。由于对学者的赞助,长期以来,吴家已被接纳为地方精英的一分子;通常的情况下,这已能给吴家有效的社会保护。而且吴家又非常实际的捐了三十万两银给国库,家中有六人取得七品京官衔。以吴家新获得的正式官员身分,配合其财富;因此使他们毫无困难地占有黄山的木材,孰料天启六年(1626),因一个背叛的仆人告到一个贪婪而有权力的宦官那里,夸大吴家霸占公共山地的说法;于是,不但吴氏所有在徽州地区的家产被政府没收,而且他在天津、河南、扬州、与杭州各地的盐业与当铺的各种投资,都遭调查,最终都被政府没收。
这些事例并不限于徽州地区,也不限于晚明。十八世纪前半期的雍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有另一个生动地描述扬州大盐商万雪斋的例子;扬州位近大运河与长江交会处,是个文化中心和奢华消费城市。即使以扬州的消费标准而论,万氏招待著名文士的方式,也被认为是奢侈浪费的。他的七姨太有些文学天分,热心社交,就组织了个诗会。尽管万雪斋有精英的身分,他还是成为贪婪成性的地方官下手的对象;经过与宠爱的七太太深思熟虑之后,万雪斋决定从他正迅速缩水的家产拿出一万两银子,去买一个边远的贵州省知府实缺,因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买得一个立刻可以上任的高官,万雪斋才能逃脱他与其姨太太认为正逼近的死亡危机。吴敬梓在评论万雪斋的事例时,引用了一句包含当代基本社会事实的通行中国俗语:「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
李贽较为人知的是笔名李卓吾(嘉靖六年至万历三十年,1527-1602)。他做过地方官,也是思想界的离经叛道者,曾做过大略的观察:「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众,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 这也是明清时代商人常为官员立碑以表达谢意的原因,因为只有受到那些有同情心官员及时保护,商人才得以免受地方政府的吏员及其手下的威胁与榨取。
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小说《官场现形记》在序文中说到明清社会权力的根源: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一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农、工、商分为「四民」;各事其事,各业其业;上无所扰,亦下无所争。其后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若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
以上的实例与观察无疑地包涵了相当多的社会实况,然而这不应扭曲我们对事情的真正了解。其一,这些被官员勒索而终致破产的商人案例,虽有启发性,却是例外而非常态。其二,财富是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虽然理论上其重要性还不及高阶功名与官职,但财富真实的力量随时间的前进而稳定成长。在景泰二年(1451)以前,财富最多不过能帮助人得到较好的教育机会,便利最终达成高等功名或官位而已;直到当时选官之法,完全由正途的科举或特别的保荐、或由国子监监生、吏员和胥吏升迁。但由于正统十四年(1449)士木之变,蒙古瓦剌入侵,严重地威胁首都北京,迫使明政府不得不开捐纳官位、官衔与国子监生之例,为富人的社会流路开启重要的前管道迈开了一大步。长久看来,贩售官位与官衔及国子监生资格,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远比法国旧政府(ancien regime)实行的波莱特制度(Institution of la Paulette),在促进中产阶级(bourgeoisie)上升为贵族的影响要大得多。
从当代的士人与官员部分的统计资料与证词,我们得知明代卖官位、官衔与监生资格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崇祯十七年(1644)早春,北京陷落之后,一个明朝的亲王(福王)在南京即位,继续抗清。他的主要筹饷方法就是大规模地卖官鬻爵。这个流亡政权的卖官,随着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下南京而终止。但这个卖官政策对清初的政策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清朝政府在1660和1670年代(顺治朝及康熙朝前期),需钱孔亟,首先是为供应南方强大的三藩,然后是供应平定三藩之需。的确,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678-82),清朝政府不但大规模地卖官,而且几乎是史无前例地,全国性地进行生员资格贩卖。虽然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附,全国平定之后,生员资格贩卖政策永远不再继续实行,但每逢军事出征、重大天灾及兴建公共工程时,仍常以捐官来解决财政需求。
我们无法确知清代前半期捐官的数量,但难能可贵的一件嘉庆三年(1798)名单透漏了那年捐官的数字:京官1,437、省级与地方官3,095,这还不包括许多从九品以下及不入九品之流的下级官员。其中最大宗的是县丞1,258,其次是笔帖式547,他们是京官捐买之最大宗。其中甚至还有十岁以下男童的捐官案例,因为捐了官之后不是马上可以上任,得等一段时间,早捐就可早任官。虽然这不是常例,不会每年都捐这么多官,但嘉庆三年这年捐官的总数4,532,已超过中央政府品官总数至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再加上嘉庆四年至道光三十年(1799-1850)捐监人数 ,显示至少在清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金钱直接转换成高社会地位,远比明代容易得多。
官员中捐官的比例有多少,可由分析两种官员初任官职资格的系统性资料得知。第一种,是各种版本的《爵秩全览》,也就是官员品级与俸禄的手册,在北美能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中期(乾隆中期),最大宗的是十九世纪(嘉庆至光绪)。其中一个样本显示,经过百多年,中央政府官员中正途(高阶科名与荫叙)与非正途(如捐纳等)出身的比例,只有相当小的变动。这是因为习惯上,某些中央政府官职员额,分别保留给正途与非正途出身的人。例如,高官与学官,照例是保留给高阶科名出身的人,某种官职,特别是「笔帖式」,也就是满人书记,是保留和供满、蒙、汉军八旗捐纳的。六部与其他几个中央机关的三个等级的笔帖式,也按一定比例分配。随着捐纳的笔帖式人数逐渐增加,一种叫做额外主事的额外资浅书记人数也相对增加,这个额外主事的位子通常是拨给新科进士的。为平衡起见,通常中央政府官员中,正途出身的人数,比非正途出身的人数,在幅度上要稍多一点。
正途与非正途出身官员比例之变迁,可由分析地方官员初任官职资格的资料,更好地呈现出来。由于要对那些不计其数的「佐杂」,也就是最低的两个品级(八品与九品)地方官做完整分析非常费时;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清末,这些八、九品的官员,其职位大部分是捐纳来的。因此,我们分析官员的出身,只限于地方行政的中坚,即四品至七品的地方官阶级。我们选择了可以代表十八世纪后半、十九世纪前半与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官吏人名录《爵秩全览》,以见证捐官急速增长的趋势。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帝国正值和平、繁荣与行政秩序井然的巅峰,这一年的《爵秩全览》中登录的地方官员中,超过70%是贡生以上正途出身的。道光二十年(1840),当国家仍处于和平之时,非正途出身的官员增加的百分比并不太大。但是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64)的太平天国之乱,迫使清廷卖官,其规模之大,是以前做梦都梦不到的。乱事平定之后,非正途出身官员的百分比一直都超过正途出身者。
上述数据的资讯并不完整,《爵秩全览》并未指明那些最初以正途出身官员,是否再度捐纳,或甚至在初任官员时就以捐纳做为其加速进入仕途或晋升的手段。第二类的数据是《同官录》,也就是各省官员的人名录,比较令人满意。由于《同官录》未包含大量的「佐杂」,因此我们只能分析七品以上省级与地方官员的出身背景。
光绪十二年(1886)版的浙江官员《同官录》相当完整,包括佐杂及府州县学的教授、教谕等,特别具启发性。府州县学的教官做为一个群体,有别于任官常规的例子,是格外孤单而可悲。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决定官员身分的因素中,金钱远比学术来得重要。90名教官中,60名出身正途,26名捐纳,4名保举;但60名出身正途的教官之中,又有26名进一步以捐纳取得官职。在排除大量以捐纳取得从九品官位及不入流的吏员之后,剩下的272名佐杂中有238名取得官位唯一的方式是捐纳。
系统性的统计资料之外,个人的传记证明,大部分情况下,在捐纳官位之前,需要物质帮助才能得到好的教育,高的功名,最终达到官员的身分地位。这一事实,或可以一些出身贫寒而奋斗不懈的学者来说明。例如沈垚(嘉庆三年至道光二十年,1798-1840)是道光十四年(1834)的「优贡生」,也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曾做如下的一般性观察:
[自宋以后]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非父兄先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
沈垚从他与一些天资好却遭挫折的朋友们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当今钱神为贵,儒术道消」。尽管这一印象想来是夸大而单方面的看法,也很可能只适用于清代后期;但能帮助现代学子了解,一般认为明清时代全国竞争性的考试体制下,只靠个人的才能就能决定个人社会价值与地位的看法,是多么地夸张。
总之,从我们所举的实例与全体的统计,可清楚地知道,在明清时代的中国,钱财本身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它必须转化成官员身分,才能让人充分感到钱财的力量。从明朝创建到蒙古入侵的正统十四年(1449),财富只能间接地帮助获得一个较高的功名与一个官职。景泰二年(1451)以后,不时出现的卖官,对富人开启一条社会流动的新管道,使钱财在决定社会地位上,成为重要性不断增强之因素。但直到太平天国叛乱的咸丰元年(1851),国家一直把科举制度,做为首要的社会流动管道,捐纳做为次要管道。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后,国家开始失去其管理控制能力,钱财的重要性才超过高等功名,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早期近代及近代的社会阶层,我们发现其间只是程度不同,而非性质的相异。劳力者与劳心者的界线,儒家中国可能比西方来得清晰;但这样的界线,在所有的前近代与近代的文明社会差不多都存在。即使在现代的北美,虽然对劳力者的偏见已是最少的,但社会阶层体制的根本区别,仍在白领与蓝领职业之间。儒家传统与价值,可能会对富人在得以进入统治精英时造成较大的压力,但同样的驱策与社会弱势情结,也在大多数前近代与近代社会的新富(nouveaux riches)身上可以看到。教育,或更准确地说大学学位,在最「物质主义化」的北美社会阶层,越来越重要。甚至传统中国对各阶级生活方式详细的法律规定并非独一无二,中古与后封建时代的欧洲也有同样的情况。明清社会特别之处,在于除了这五个半世纪时期的最后六十年之外,官僚制度与国家权力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一直是管控社会流动的主要管道,这多少符合当时确立已久的儒家传统的指导原则。[三民网路书店]